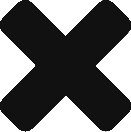文|張依婷
女人迷 Womany 2019/03/9
C 問我下課後能不能講中文,我說:「可以啊,只是我通常不喜歡跟學生講中文,因為怕被佔便宜,也擔心遇到對台灣身認分同反感的中國學生。」她說:「但其實不是每件事情都要講到政治或國籍啊。」
並不是每件事情都要講到政治,但政治卻緊密連結著我們日常生活。我無法說 C 說的是錯的,卻也無法完全認同。
「老師,妳是中國人嗎?」來自中國北方一省的 C 瞪著大大的眼睛,小聲地用英文問我。C 是我在賓州州立大學寫作中心指導的大一學生,金框的鏡片後面是一張帶有雀斑的小臉,頭髮梳得整整齊齊的,笑起來天真可愛。
雖然早有預感 C 會對我提問,畢竟我有一張東亞人的臉孔,用的名字又是中文的羅馬拼音,但當下還是愣了愣地搖搖頭。C 更加困惑了,繼續用英文問我:「那妳是哪裡來的?」
「我是台灣人。」
「台灣 ?台灣不就是中國的嗎?妳不就是中國人嗎?」
「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。我是台灣人。」
我用英文簡短地回答,C 似乎不知所措,還以為自己聽錯了。
「妳⋯⋯妳說的是泰國嗎?泰國不是中國的一部分,但台灣是。」
「我說台灣。我是台灣人。」
類似的對話在我過去三、四年的留學生涯中層出不窮,相信這也是許多在海外留學、工作的台灣人的經驗。雖然並不是每一位在台灣成長生活的人都認同自己是「台灣人」,擁抱這個身份的人大概都知道,這樣的認同意味著在各個場合不斷地為自己解釋、辯護。有時候因為害怕場面尷尬,我們也會選擇沈默,甚至離開。
來自非常保守的家庭的我,大學畢業以前沒有認真想過台灣與中國的關係,只覺得政治身份以及文化認同是很龐雜的議題。來到美國以後,因為研究的主題,逐漸開始釐清了台灣複雜的殖民歷史以及台灣在太平洋世界、中美關係之中扮演的微妙角色。
身份認同帶給我們提出異議、改革創新的力量,也造成意識高牆與衝突撕裂。身份議題如此敏感,想必是因為它逼著我們探觸自己最脆弱的部分,關於如何建構「自己」,以及如何與他人建立連結。
在賓州做研究與教課的這幾年,我常常思考著自己與來自中國的學生之間的關係,關於師生之間的權力不對等,以及我們極度不同的知識觀與世界觀。 身份的問題是複雜的,例如教授高年級商業、技術寫作課程時,我時常考慮要不要與來自中國的國際生說中文。我了解在白人為主的賓州鄉下作為黃種人的孤立感,所以開始教書的頭兩年,我會主動告知學生我來自台灣、會講中文。大部分的中國學生都很高興我們能用中文溝通,也好好把握每個能夠討論、學習的機會。但我也曾遇過幾位想要因此而佔便宜、拉攏關係的學生。後來,為了保護自己,也為了學生們的學習狀態著想,我一律與學生說英文,也不再解釋自己來自哪裡。
過往三四年,我一次又一次遇見來自中國的學生、朋友、同事、教授,這些邂逅卻沒有辦法變成我們用以理解中國人與台灣人關係的公式。每一次的邂逅都因為彼此的生命經驗以及當下的時空,而有了很不一樣的結果,像是我遇見了能夠彼此提攜、相互珍惜的朋友,天真善良的學生,溫和有學養的老師,當然也有因為無法接受彼此立場而不想深入往來的人。每一種關係都各有它的奇妙,國籍認同似乎不是宰制我們連結的全部。
每一次遇見中國的朋友或學生,我總明確表達自己的臺灣身份認同、台灣的特殊性。解釋自己是台灣人其實也不是為了證明什麼, 更不是透過比較身份之間的高低好壞去創造對立,不過就是平實闡述我們複雜的歷史成因,我們因為島嶼地形、殖民歷史、族群多元造成的獨特性。我們就像世界上任何一種身份一樣,都是那樣獨特。
但多次的解釋以及身處弱勢的經驗,也讓我思考,我是不是也曾是那位沒有用力去理解與傾聽他人身份認同的人。當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宣稱自己是台灣人的時候,我們所構想的「台灣人」有包括台灣的原住民嗎?同志朋友、雙性人、跨性別者呢?台灣的新移民呢?混血兒呢?
我們是不是也曾像那些不認同我們的中國學生、友人一樣,在確認自己的身份認同同時,忘了反思我們對自己身份狹隘的定義,忘了探問:我們的身份與社群認同能不能變得更寬廣,去涵納不同的元素,無論是性別、性向、種族與宗教?
其實,從過往幾年為自己所思所想辯護的經驗中,讓我感到最震撼的不是那些解釋與確立自己身份的快感,而是在說服他人的過程中,我發現任何一種身份都能夠被擴大與深化。如果要讓我們所擁護的身分、文化保持活力,我們必得不害怕接觸與自己不同的觀點,並瞭解到身份這種東西是流動的,會改變,也能創造新的連結。這樣的心情,使我期待看見能夠海納不同知識觀、生命經驗、生活方式的「台灣人」。
經過了那一次有點緊張的談話後,C前幾天又像往常一樣來寫作教學中心找我。她手拿著剛從星巴克買來的果汁,興奮地跟我說著她很想趕快畢業回中國賺錢、帶年老的爺爺奶奶去紐西蘭玩,我們也聊到了她未來想念社會學或犯罪學,而她的選擇是如何跟父母的期待背道而馳。我忽然覺得我們的心情與經驗有一些相似。
C 問我下課後能不能講中文,我說:「可以啊,只是我通常不喜歡跟學生講中文,因為怕被佔便宜,也擔心遇到對台灣身認分同反感的中國學生。」她說:「但其實不是每件事情都要講到政治或國籍啊。」
並不是每件事情都要講到政治,但政治卻緊密連結著我們日常生活。我無法說 C 說的是錯的,卻也無法完全認同。畢竟,對於處於政治弱勢的族群而言,被壓迫的痛苦與焦慮感是如影隨形的。不過,我們的確不能只考慮到國籍,因為政治弱勢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,包括性別、性向、族群、信仰、文化資本、城鄉差距、教育等等,所有你能想得到、那些造就我們生命不同的元素。
下一次有中國的學生或朋友問我是不是中國人的時候,我還是會堅定自信地說我是台灣人。 表達自己的同時,我也期許自己能夠靜觀與自己立場不同的人。而更我希望牢記這樣的經驗,在每一次不同的邂逅中,都能看見每種身份、生命經驗的相似處,也承認我們的不一樣。